直到上英语课时接触 “脑腐(brain rot)” 概念,答案逐渐清晰。


据牛津大学的说法,它最早出现在1854年亨利·大卫·梭罗出版的经典著作《瓦尔登湖》中,梭罗在讲述了他独自搬到林中小屋的故事时提到了这个词:
“While England endeavors to cure the potato-rot,” Thoreau lamented, “will not any endeavor to cure the brain-rot, which prevails so much more widely and fatally?”
“当英格兰努力治愈土豆烂病时,难道没有人努力治愈更广泛、更致命的脑腐吗?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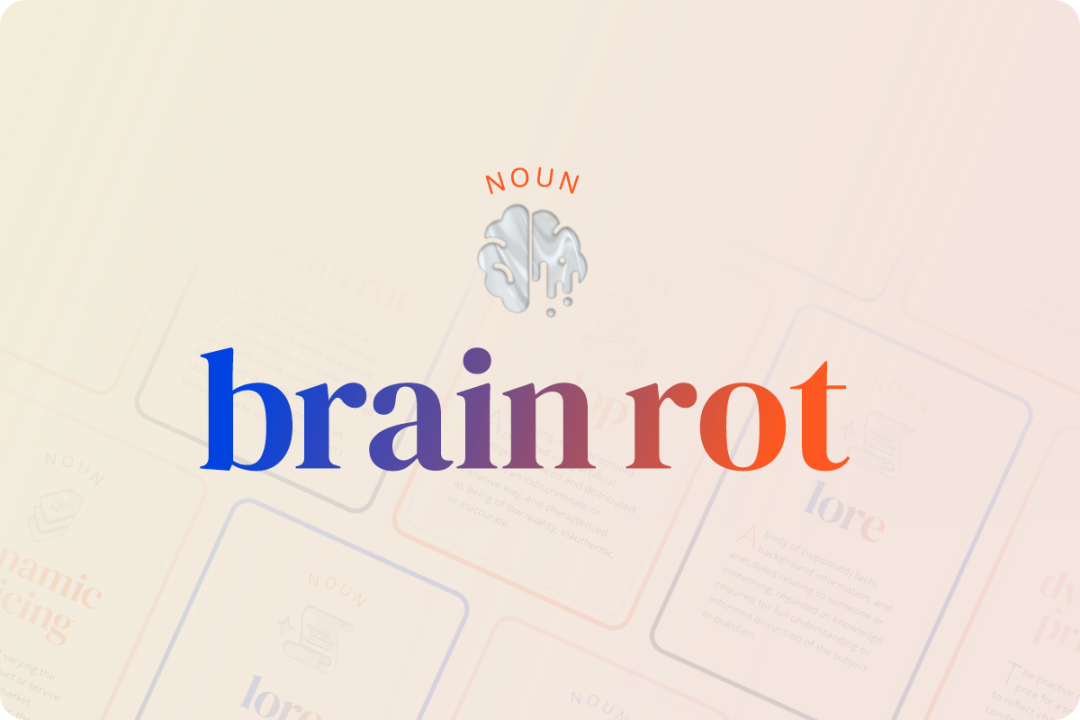
薛定谔曾说 “人活着是对抗熵增”,而 AI 时代,我们还需对抗 “脑腐”。
大脑天然倾向 “省力”,AI 恰好提供了最优省力路径:无需查资料,AI 可总结;无需理逻辑,AI 可梳理;无需组文案,AI 可生成。
但这种 “省力” 本质是大脑的 “主动躺平”—— 我们将本该完成的 “思考闭环” 拱手相让,久而久之,思维便如长期不锻炼的肌肉,逐渐失去力量。

遇问题第一反应是 “问 AI”,而非先翻权威资料、拆解问题核心;读文章依赖 AI “重点摘要”,跳过需咀嚼的段落,丧失梳理逻辑的耐心。
这类行为看似省时,实则持续消耗思考力 —— 如同吃他人嚼过的饭,虽能果腹,却失却食物本味,更无法锻炼自身 “咀嚼” 能力。
“脑腐” 的可怕之处,正在于让我们从 “思考者” 退化为 “AI 传声筒”。

依赖 AI 是典型的思维惰性:快速获结果如尝甜糖,当下满足却转瞬空虚;主动思考需耗时查资料、耗力理逻辑,甚至承受试错挫败,但最终得出答案时,“能独立解决问题” 的踏实感,是 AI 无法提供的。
AI 时代的 “下坡路”,本质是放弃大脑的 “思考权”。

给 AI 设 “边界”:不让 AI 处理 “自身可完成” 的事。如查问题时,先在纸上明确 “核心需求”“所需信息类型”,通过权威渠道初步验证后,再用 AI 补充未考虑的维度,让 AI 回归 “助手” 而非 “替身”。
留 “无 AI 时间”:每日固定时段关闭 AI 工具,选择深度阅读(非 AI “精华解读”)或手写日记 —— 即便记录零散,也能倒逼大脑主动梳理想法。
借小事锻炼思维:脱离 AI 指导完成具体事务(如按自身经验调整菜谱用量),从试错中积累独立判断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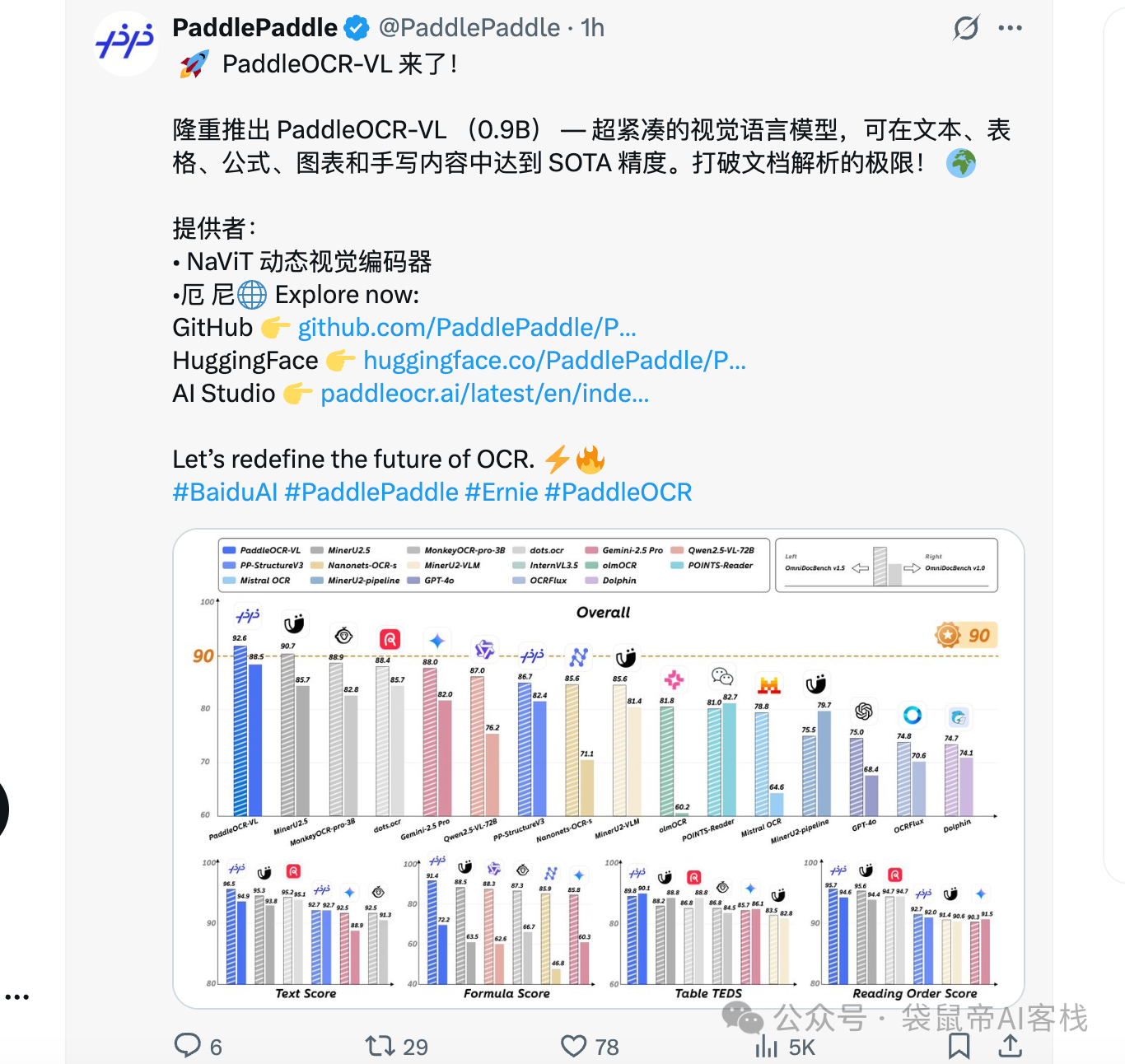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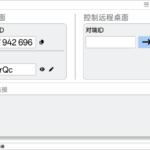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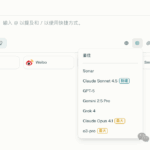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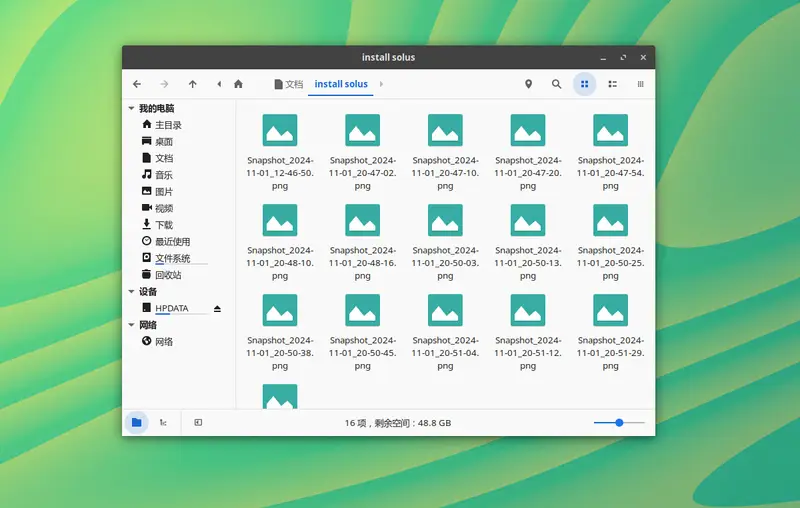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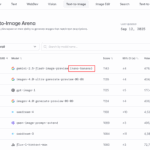

评论 (0)